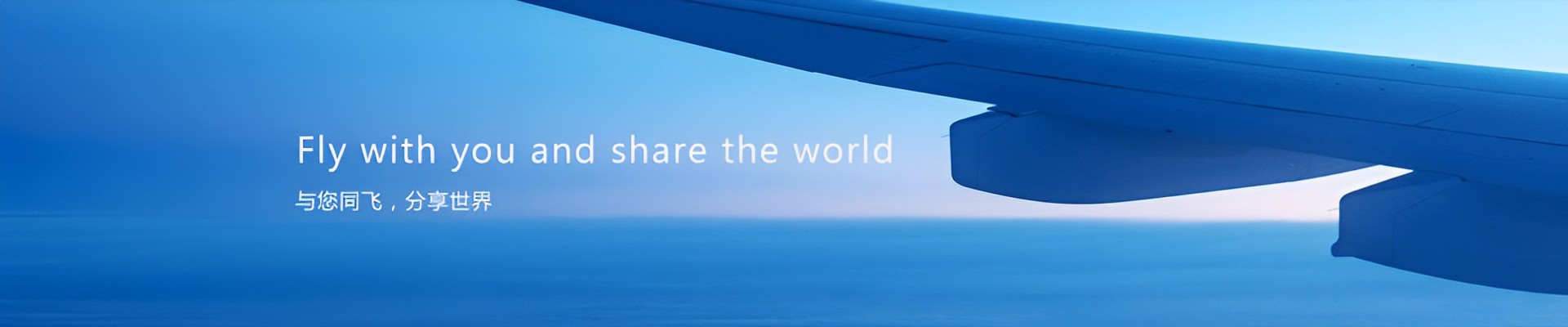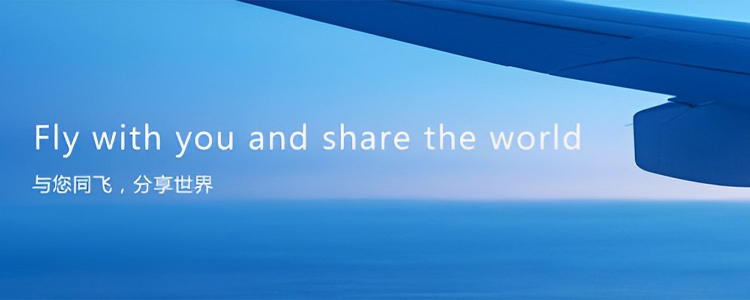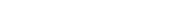2020年注定不一样,人们还没从疫情的惶恐中缓过神来,一桩“横空”爆出的商界巨鳄猥亵幼女案,又重新聚焦了人们的关注。连日来,有关轻判的质疑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对王振华不认罪和陈有西无罪辩护的讨伐声,更是堪比这雷暴天气中汹涌袭来的泥石流,奔腾不息,毫无退意,大有吞噬王、陈之势。
诚然,该案的一审判决没有取得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诚如张明楷教授所言: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民众虽不满5年判决,但没有诋毁法律和责怪法官,众人之所以集中“炮火”猛烈轰炸王振华,显然在于事件本身的反人伦性,而陈有西的“不检点”,则自然被划在射程范围。
笔者不苟同一审法院认为王振华不具有“其他恶劣情节”只能在5年以下从重判处的观点和判决结果,认为王振华当在15年以下(5年以上)幅度刑内从重判处,这并非受民意裹挟之下的义愤之言,而是基于理性分析。分析系基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即王振华有猥亵行为,小女孩的阴道撕裂伤系王振华造成且构成轻伤二级正确无误为前提。
事实清楚了,剩下的就是法律问题了。
刑法第237条第2款规定,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注:这里的“五年以上”未设定上限,理论上当然可“上”至有期徒刑的上限15年);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罚。该条“其他恶劣情节”,是2015年刑(九)修正案新增的,遗憾的是,修正案并未就何为“其他恶劣情节”作出明确规定,给裁判法官着实带来不小的困扰,就像迷雾中只能看到隐约的灯盏,怎么利用好它指引方向,是考量智慧和胆识的。
但是,认定“其他恶劣情节”真的就无迹可寻吗?
早在2013年,两高两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性侵意见》)第25条规定,针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更要依法从严惩处:…(3)采用暴力、胁迫、麻醉等强制手段实施奸淫幼女、猥亵儿童犯罪的;(4)对不满12周岁的儿童、农村留守儿童、严重残疾或者精神智力发育迟滞的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5)猥亵多名未成年人,或者多次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6)造成未成年人被害人轻伤,感染性病等后果的;(7)有强奸、猥亵犯罪前科劣迹的。从条文语义逻辑看,该条第一层次的“从重处罚”仅针对性侵对象是未成年人的,与刑法第237条第1、3款在5年以下从重处罚的规定吻合。而第二层次的“更要依法从严惩处”则是以满足罗列的7种情形之一为前提的,该7种情形下,要么指犯罪行为人手段恶劣,要么指被害人系特别弱势的未成年人,条文中的“更要+从严”,在量刑上显然是要超出第一层次(5年以下)的“从重处罚”情形,属于拉升量刑档次,提档升格的情形,这也与刑法第237条第2、3款规定的五年以上量刑情形相契合。否则,如果仍理解为在5年以下幅度刑内从重处罚,则该条文字就没有必要这样表述了,直接表述为“针对未成年实施强奸、猥亵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237条第1款规定从重处罚…”即可。
据此,本案王振华的行为应当认定“具有其他恶劣情节”。
第一,王振华有猥亵行为,并造成9岁幼女的阴道撕裂伤达到轻伤二级,完全符合《性侵意见》第25条第(4)、(6)项规定;第二,王振华雇请对其“好色”胃口了如指掌的同伙(昔日旧情人)周燕芬通过哄骗利诱“猎”来2名幼女,王振华选了一个9岁女孩,事毕后支付周燕芬10万元“感谢费”,可见其有犯罪预谋,且性侵手段、方法、对象、后果(小女孩被性侵后一听说“上海”,就因恐惧而哭泣)等,已经明显超出“一般”猥亵行为的罪孽和危害程度,不可谓不恶劣。
一审法院仅把对9岁幼女的猥亵和造成的轻伤二级看成是“严重后果”,而不算“恶劣情节”,这是令人费解的。如果这还不算,那么,性侵一两岁的幼女,并/或者造成重伤,又能否算呢?按照一审法院的审判思维和认定逻辑,依然可能是找不到适用标准,这是比较可怕的。
“后果”(包含“结果”,“后果”涵盖的事实外延更大)是一种事实状态,与“情节”涵盖的事实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包含关系(后者包含前者)。只是犯罪情节涵盖的事实,并非指构成犯罪的主、客观要件的基本事实,而是排除了决定犯罪性质的基本事实以外的其他能够影响危害程度的那些犯罪事实,一般包括犯罪时间和地点、手段和方法、动机和结果、犯罪的具体对象、行为的一贯表现以及犯罪后的态度等,而“恶劣”相对于“一般”而言,系从“情节”本身出发,看对法益的侵害和公众的情感接受程度等因素,而进行的评价。
一审法院将对9岁幼女的猥亵和造成的轻伤二级之事实,仅看成是“严重后果”,而不认为是“恶劣情节”,一错是混淆了两个概念的本质(是包含的,而非排斥的);二错是法律解释的原理没有正确使用。因为,如果法律规定不明(比如刑法本身没有具体规定什么是“其他恶劣情节”,而《性侵意见》虽内容具体但没有明确为认定标准及如何适用于量刑),那么,在必须作出法律判定的情况下,是进行扩大解释还是缩小解释,是保守解释还是与时俱进解释,是体系解释还是局部解释,是需要认真考量的,最基本的判断,是要顺应“天理人情民意”,这也是广义上的法律,是两高近年来经常提出的司法理念,不容忽视,否则,治理社会赖以适用的“国法”就将失去生命力。
结论:王振华当在15年以下(5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从重处罚(再次重申:本文系建立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王振华辩解没有猥亵行为,陈有西“妄言”小女孩的阴道撕裂伤属于陈旧伤甚至之前有过性行为,辩方的“专家”论证意见等均不成立基础上的,否则,笔者的观点和结论均需修改)。
未成年人需要特殊保护,幼女的性权利更需要重点且特别保护,她们天真无邪,看世界一切美好,对“性”认知不能,缺乏防卫意识和能力。但多年来屡屡曝出反人伦的性侵幼女案,一次次触及公众底线,极大伤害了民众情感和社会正义价值观。刑法的行为规范示范作用和社会治理的惩治功能,如何充分有效发挥,法律人需要努力,社会各界均需要行动。
无论王振华案最终结果如何,民众都应保持理性。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个案公正,更需要整个法治体系的公正,实现“天理、国法、人情、民意”四维统一,不断赋予司法审判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记得《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曾经说过:个案是时代的符号,最大限度地防止司法不公和冤错案件,需要在每一宗个案裁判中捍卫公正、引领价值,真正作出无愧于法律、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判决,让一个个充满公正、智慧的判决,成为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重要力量。
诚如典型的“昆山反杀”案,激活僵尸法条“正当防卫”一样,期待王振华案能终结法律保护幼女性权利“宽松软”的不力状况,开启强力保护新篇章。
作者简介
刘明银律师,北京蓝鹏(合肥)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执行主任,刑事业务团队负责人。在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和辩护技巧,办理过一些省内外有影响的大要案,成就了多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或不起诉、无罪释放的经典案例。
手机:13605516056(微信同号)
律所地址:合肥市徽州大道与扬子江路交叉口金融港A6栋13层
2020年注定不一样,人们还没从疫情的惶恐中缓过神来,一桩“横空”爆出的商界巨鳄猥亵幼女案,又重新聚焦了人们的关注。连日来,有关轻判的质疑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对王振华不认罪和陈有西无罪辩护的讨伐声,更是堪比这雷暴天气中汹涌袭来的泥石流,奔腾不息,毫无退意,大有吞噬王、陈之势。
诚然,该案的一审判决没有取得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诚如张明楷教授所言: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民众虽不满5年判决,但没有诋毁法律和责怪法官,众人之所以集中“炮火”猛烈轰炸王振华,显然在于事件本身的反人伦性,而陈有西的“不检点”,则自然被划在射程范围。
笔者不苟同一审法院认为王振华不具有“其他恶劣情节”只能在5年以下从重判处的观点和判决结果,认为王振华当在15年以下(5年以上)幅度刑内从重判处,这并非受民意裹挟之下的义愤之言,而是基于理性分析。分析系基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即王振华有猥亵行为,小女孩的阴道撕裂伤系王振华造成且构成轻伤二级正确无误为前提。
事实清楚了,剩下的就是法律问题了。
刑法第237条第2款规定,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注:这里的“五年以上”未设定上限,理论上当然可“上”至有期徒刑的上限15年);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罚。该条“其他恶劣情节”,是2015年刑(九)修正案新增的,遗憾的是,修正案并未就何为“其他恶劣情节”作出明确规定,给裁判法官着实带来不小的困扰,就像迷雾中只能看到隐约的灯盏,怎么利用好它指引方向,是考量智慧和胆识的。
但是,认定“其他恶劣情节”真的就无迹可寻吗?
早在2013年,两高两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性侵意见》)第25条规定,针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更要依法从严惩处:…(3)采用暴力、胁迫、麻醉等强制手段实施奸淫幼女、猥亵儿童犯罪的;(4)对不满12周岁的儿童、农村留守儿童、严重残疾或者精神智力发育迟滞的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5)猥亵多名未成年人,或者多次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6)造成未成年人被害人轻伤,感染性病等后果的;(7)有强奸、猥亵犯罪前科劣迹的。从条文语义逻辑看,该条第一层次的“从重处罚”仅针对性侵对象是未成年人的,与刑法第237条第1、3款在5年以下从重处罚的规定吻合。而第二层次的“更要依法从严惩处”则是以满足罗列的7种情形之一为前提的,该7种情形下,要么指犯罪行为人手段恶劣,要么指被害人系特别弱势的未成年人,条文中的“更要+从严”,在量刑上显然是要超出第一层次(5年以下)的“从重处罚”情形,属于拉升量刑档次,提档升格的情形,这也与刑法第237条第2、3款规定的五年以上量刑情形相契合。否则,如果仍理解为在5年以下幅度刑内从重处罚,则该条文字就没有必要这样表述了,直接表述为“针对未成年实施强奸、猥亵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237条第1款规定从重处罚…”即可。
据此,本案王振华的行为应当认定“具有其他恶劣情节”。
第一,王振华有猥亵行为,并造成9岁幼女的阴道撕裂伤达到轻伤二级,完全符合《性侵意见》第25条第(4)、(6)项规定;第二,王振华雇请对其“好色”胃口了如指掌的同伙(昔日旧情人)周燕芬通过哄骗利诱“猎”来2名幼女,王振华选了一个9岁女孩,事毕后支付周燕芬10万元“感谢费”,可见其有犯罪预谋,且性侵手段、方法、对象、后果(小女孩被性侵后一听说“上海”,就因恐惧而哭泣)等,已经明显超出“一般”猥亵行为的罪孽和危害程度,不可谓不恶劣。
一审法院仅把对9岁幼女的猥亵和造成的轻伤二级看成是“严重后果”,而不算“恶劣情节”,这是令人费解的。如果这还不算,那么,性侵一两岁的幼女,并/或者造成重伤,又能否算呢?按照一审法院的审判思维和认定逻辑,依然可能是找不到适用标准,这是比较可怕的。
“后果”(包含“结果”,“后果”涵盖的事实外延更大)是一种事实状态,与“情节”涵盖的事实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包含关系(后者包含前者)。只是犯罪情节涵盖的事实,并非指构成犯罪的主、客观要件的基本事实,而是排除了决定犯罪性质的基本事实以外的其他能够影响危害程度的那些犯罪事实,一般包括犯罪时间和地点、手段和方法、动机和结果、犯罪的具体对象、行为的一贯表现以及犯罪后的态度等,而“恶劣”相对于“一般”而言,系从“情节”本身出发,看对法益的侵害和公众的情感接受程度等因素,而进行的评价。
一审法院将对9岁幼女的猥亵和造成的轻伤二级之事实,仅看成是“严重后果”,而不认为是“恶劣情节”,一错是混淆了两个概念的本质(是包含的,而非排斥的);二错是法律解释的原理没有正确使用。因为,如果法律规定不明(比如刑法本身没有具体规定什么是“其他恶劣情节”,而《性侵意见》虽内容具体但没有明确为认定标准及如何适用于量刑),那么,在必须作出法律判定的情况下,是进行扩大解释还是缩小解释,是保守解释还是与时俱进解释,是体系解释还是局部解释,是需要认真考量的,最基本的判断,是要顺应“天理人情民意”,这也是广义上的法律,是两高近年来经常提出的司法理念,不容忽视,否则,治理社会赖以适用的“国法”就将失去生命力。
结论:王振华当在15年以下(5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从重处罚(再次重申:本文系建立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王振华辩解没有猥亵行为,陈有西“妄言”小女孩的阴道撕裂伤属于陈旧伤甚至之前有过性行为,辩方的“专家”论证意见等均不成立基础上的,否则,笔者的观点和结论均需修改)。
未成年人需要特殊保护,幼女的性权利更需要重点且特别保护,她们天真无邪,看世界一切美好,对“性”认知不能,缺乏防卫意识和能力。但多年来屡屡曝出反人伦的性侵幼女案,一次次触及公众底线,极大伤害了民众情感和社会正义价值观。刑法的行为规范示范作用和社会治理的惩治功能,如何充分有效发挥,法律人需要努力,社会各界均需要行动。
无论王振华案最终结果如何,民众都应保持理性。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个案公正,更需要整个法治体系的公正,实现“天理、国法、人情、民意”四维统一,不断赋予司法审判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记得《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曾经说过:个案是时代的符号,最大限度地防止司法不公和冤错案件,需要在每一宗个案裁判中捍卫公正、引领价值,真正作出无愧于法律、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判决,让一个个充满公正、智慧的判决,成为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重要力量。
诚如典型的“昆山反杀”案,激活僵尸法条“正当防卫”一样,期待王振华案能终结法律保护幼女性权利“宽松软”的不力状况,开启强力保护新篇章。
作者简介
刘明银律师,北京蓝鹏(合肥)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执行主任,刑事业务团队负责人。在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和辩护技巧,办理过一些省内外有影响的大要案,成就了多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或不起诉、无罪释放的经典案例。
手机:13605516056(微信同号)
律所地址:合肥市徽州大道与扬子江路交叉口金融港A6栋13层